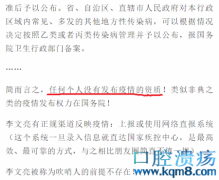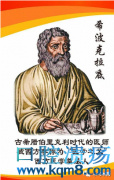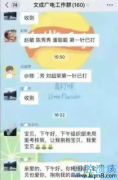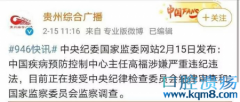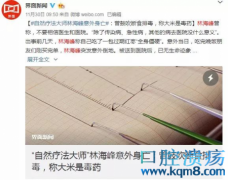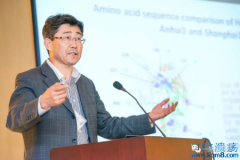今年1月23日,管轶接受财新记者采访,说这次疫情的感染人数起码是非典的十倍以上,之后他说自己做了逃兵,离开了。
很快,嘲讽批评的文章大量出现,管轶成了钟南山院士的反面映衬。
今天,全国累计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超过了五万九千人,是非典时期的十倍还多,管轶的预测成了实情。
2003年非典爆发时,钟南山与管轶结识,体制内外的两人通力合作,找出了非典病原体,为终结疫情提供了重要的报告。

2002年12月,广州出现了第一例非典病例,接着一些医护人员出现症状。
2003年2月8日,管轶从江西老家回到香港,他的妻子说,有很多人从深圳来香港买醋。
当时病情已经开始蔓延,管轶上网查资料,发现珠三角好几个城市都有异常。
第二天,他决定介入调查,去了广州。
2月11日,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,第一次通报内地的患病情况。
当时305个感染者中105人是医护人员,死亡5人。
钟南山知道管轶的流感实验室,当天就跟他签了协议,双方合作调查病因,钟南山这边提供病人样本,管轶负责分离病毒,对结果达成共识再作汇报和发布。
2月12日上午,管轶要去医院取标本,因为两地合作有各种规定,钟南山没有让他进病房,而是按他的要求提供了样本。
下午管轶把标本包好,坐直通车背回了香港。
理论上,这属于越界带运标本,但这次情形特殊。
两三天后,管轶的实验室有了结果。
因为香港那几年接连爆发禽流感,且刚刚又出现了家庭感染事件,所以管轶当时判断是禽流感病毒,但他取回的标本中发现了多种病毒,就是没发现禽流感。
管轶当时认为结果和预判不一致是标本取得不好。
他决定一个人再去广州取一次标本。
而此时,内地的媒体公布病毒的病原体找到了,是衣原体。

2月18日,公布病原体那天,钟南山院士不太高兴——之前他用治疗衣原体的办法治疗,没有效果,他可以肯定不是衣原体。
广州专家组紧急召开会议,一致认为不能简单判定衣原体是唯一病原。
2月19日,管轶到了广州,从早上10点多钟忙到下午3点半,饭都没有吃,一共取了30多个病人的标本,然后就回了香港。
2月23日清早,身在香港的管轶意外接到钟南山的电话,钟南山说自己就在他的楼下,六点半就到了。
管轶一看时间,已经8点半了,钟南山已经在楼下等了两个小时,他急忙下楼,和钟南山去广州开会。
会议上,国家疾控中心和广东疾控中心的很多专家都在,一些人认为是衣原体,而管轶认为是禽流感。
管轶坚持要带走更多样本,因为这个问题,会上爆发了激烈的讨论。
第二天,管轶得到了答复,他可以再带走6份新的标本。
也在这天,又有一个病人被确诊为禽流感。
所以管轶更执著地认为疫情是禽流感的变种。
香港大学有两个研究组在进行病毒研究,一组是管轶牵头,另一组是佩里斯。
这时,香港的SARS也爆发了,威尔斯亲王医院大量医护人员感染,有了本土的病人标本,佩里斯那一组开始注重香港本地的标本。
差不多3月18日,佩里斯那组把SARS病毒种出来了。
3月23日早晨,管轶和佩里斯一起去实验室看病毒的片子,确认是冠状病毒。
比美国早了12到24个小时。
但接下来的事情却不太愉快,管轶认为论文应该把钟南山他们也加进去,因为课题是从跟他们合作开始的。
但佩里斯不同意,理由是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标本分离出来的,不是内地的标本。
管轶觉得这太不厚道,钟南山提供的标本让他们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。
最终,佩里斯写出来的论文里依旧没有提到钟南山,管轶跟他大吵了一架。

4月,很多研究机构开始寻找SARS的动物宿主,都没有结果。
管轶判断很可能是果子狸,但当时忙着写SARS的论文,一直没有采集标本。
5月8日上午,管轶带了一个学生去深圳,从野生动物市场取了25对标本,包括了8种动物,其中果子狸取了6个标本。
管轶就是奔着果子狸去的。
5月18日上午,基因序列全部完成,管轶的徒弟已经累得从沙发上滑下去睡着了。
管轶没叫醒他,拿了三四件工作服给他盖上 5月22日晚上,管轶向《科学》杂志提交论文。
5月23日的发布会上,向公众宣布找到了SARS的病毒宿主是果子狸。
5月23日凌晨两点钟,杂志社回信,说请了两个专家审阅管轶的论文,认为是基因污染。
管轶马上回复:“你们所说的基因污染我很了解,但请你到基因库去查一查,看看管轶手上提交的基因序列有多少,这世界上还有几个人比我掌握的病毒样本更多?你们4个小时就做出这样判断是不负责任的。
” 杂志社向管轶道歉,把论文重新送出去找专家审阅。
论文最终通过《科学》杂志的审查,在线发表。
依据钟南山与管轶提供的建议,政府采取措施,禁售野生动物。
六月,天气转暖,随着大量病人被隔离救治,非典疫情终结。

接连几个月没有新增的非典病例,2003年9月,野生动物重新回到了市场上。
10月22日,管轶不放心,又去取了标本。
那天他买了9个动物,取回标本检测,有7个都是阳性。
11月份,管轶每周都会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,有时他的妻子也去取。
到12月份,市场里野生动物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。
病毒仍在人们的周围潜伏。
管轶很矛盾,疫情刚过,此时要不要上报呢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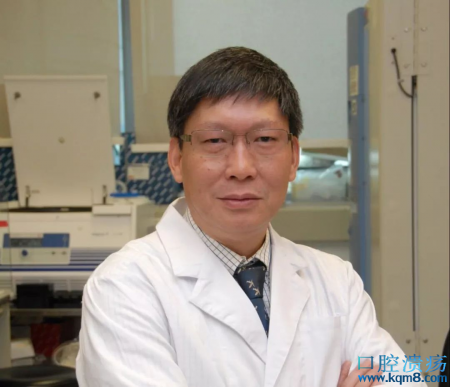
12月24日平安夜,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。
SARS如果回来就是大事,管轶决定还是要报告。
管轶总结过去的报告,写了一封信,传回北京。
后来,经过实验室的比较发现,广州新发病人的病毒,跟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。
管轶认为,唯一的办法就是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——果子狸。
根据经验,1997年香港爆发禽流感,清剿市场上的宿主动物之后,就没有病人了。
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,钟南山院士起了关键作用,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,陈述事情的严重性。
1月3日当晚,广东方面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,确定清剿果子狸的行动。
清剿从1月5日开始,1月12日结束。
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,总共有5个病人。
清剿结束之后,就再也没有新发病例了。
清剿起了作用,同时证明了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。
非典疫情结束,管轶登上《时代》周刊,被评为医疗英雄。
他说:“我没什么感觉。
这和我在科学界的地位相比差远了!” 钟南山很欣赏管轶,说:“管轶很聪明,在香港是很出名的一位微生物学家,也是禽流感方面的研究专家,一直在用心探索。
” 管轶却说:“钟南山院士比我伟大,他这样的英雄才应该多宣传。
” 2007年,管轶对整个冠状病毒的生态学做了总结,从进化角度分析,提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状病毒的源头。
之后很多年里,他和钟南山院士都在抗击禽流感的一线活跃。

2019年12月12日,优抚医院接诊了一名“不明原因肺炎”患者。
12月26日,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生张继先也发现了类似病例。
她在第二天就上报了本地疾控中心,成为上报疫情第一人。
短短几天,检测机构就检测出了与SARS高度相似的病毒,还完成了接近完整的基因组序列。
相关检测人员有些后怕:“我们非常激动及早发现并确认了这个病原体,并对患者进行了隔离,在大范围传播之前就有可能把它扼杀在摇篮中。
” 可惜,疫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,这些努力付之东流。
病例上报后的很多天里,仍然沉浸在春节即将来临的喜庆中。
随着1月份更多病例的出现,钟南山号召大家“不要去”。
1月18日,84岁高龄的钟南山登上了前往的列车。
1月20日,钟南山在媒体上宣布: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“人传人”现象。
距离第一次检测出病毒基因组序列,已过去了20多天。
一天之后,管轶也到了。
凭着多年经验,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当天下午3点,他去拜访了的“小东门市场”,看到现场,他大吃一惊,菜市场卫生状况堪忧,而且许多市民仍在热热闹闹地置办年货,哪怕钟南山已经再三强调,戴上口罩的人数还不到10%。
这次管轶仍然希望像SARS时那样,取得患者样本。
但许多本地科研机构并不愿与远在香港的研究所合作。
管轶吃了不少闭门羹后,一气之下,买机票离开了。
在机场时,他看到放行李盒子的安检小姑娘,戴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,忍不住提醒她:“丫头,你每天接触这么多旅客,这口罩质量不行。
” 他离开的当天夜里,宣布准备封城。
回到香港,财新记者问他如何看待这次封城举措,他说:“评价一个措施要看时间点和效果,时间点我觉得已经错过了黄金防控期,效果并不乐观。
”还说:“爆发是肯定的……我也算身经百战,但真的感到极其无力。
” 管轶说自己做了逃兵,回香港去隔离。
接下来,十七年前在非典中合作无间的两人,被并列在了许多新闻头条——一个“国士”,一个“逃兵”。
在几乎一边倒讨伐管轶的浪潮中,也有一些冷静的声音。
知乎上有网友说:这终归属于科学家的独立观点表达,应该得到尊重。
但更多的人开始在网上开扒管轶的所谓黑历史。
也因为管轶这番话,当天,在医院一线工作的钟南山接受了记者采访,他谨慎地说:“已对疫情做最坏打算,和广东省的病患数量没有任何隐瞒。
”似乎是对管轶的遥相回应。
1月20日以后,当地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就急剧上涨,同时疫情扩散全国。
直至今天,由于临床诊断病例被纳入确诊总数,仅湖北一天新增确诊人数就高达1.4万。

现在看来,两位处在不同位置的昔日战友,都在尽可能的尺度中讲出了真相。
最近,为了遏制疫情,一线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奔赴,做出了巨大的牺牲。
许多人只记得管轶的“狂言”,却忘了同一场采访中,他还说过:“有心无力,悲从心来。
”以及“现在不是比谁官大、比谁权力大,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”。
当年,他在确定果子狸是SARS宿主之后,在内地和香港提出宰杀果子狸,引来多方质疑。
那时他也是顶住压力说:“如果是老成一点的人,会提出多种可能,圆滑一点,留点后路,但我不想这么做。
”

2003年2月18日,管轶第二次去广州提取非典样本,他给钟南山院士打电话,没有人接。
助理告诉他,钟院士好像“中招儿”了。
管轶说,没事儿,我去见他。
那时钟南山出现了发烧、咳嗽、肺部发炎的症状。
为了不影响团队士气,他决定自己在家隔离治疗,他在门框上钉了个钉子,把吊瓶挂在上面。
晚上,管轶买了果篮去钟院士家。
钟南山的脸色不太好,但烧已经退了。
两人在沙发上对坐着,也没有戴口罩。
管轶说这次他想亲自去医院取样,钟南山点了点头。
主要参考资料:
[1]《管轶——围剿动物流感的猎人》,南方周末,2005年11月17日
[2]《管轶教授口述:2003年港大实验室是如何锁定SARS源头的?》,三联生活周刊,2013年第10期
[3]《SARS专家管轶:这次我害怕了》,财新网,2020年1月23日[4]吴靖.王晨,《失去的机会,新冠疫情早期被忽视的小医院病例》,八点健闻,2020年2月11日-END-读上一篇:《逃离的内蒙姑娘,陷入了另一场封锁》推荐阅读:《切尔诺贝利的教训:失去真相的代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