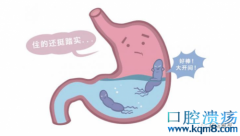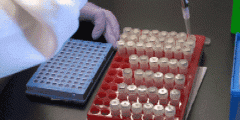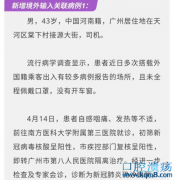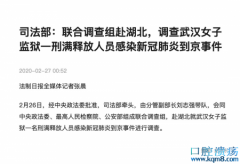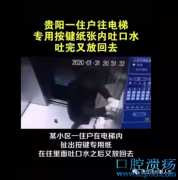还记得你所在的城市出现“第一例”时,你是怎样的状态吗? 可能震惊,可能恐慌,但医生作为最前线的接触者是最不能慌的。 今天的讲述者是位胸外科医生,他接收了当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人——病人竟然还是警车开道送来的。 接手时,医生没有防护经验,没有可参考的治疗手段,是眼前最黑暗的时候。 他只能对病人说:对不起,你这病,我也没见过。 而病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让他意外:……你不怕我吗? 这是《瘟疫瘟疫你快走》系列的第五篇。我想说,在最难的时候,希望终于来了。
怎么也没想到,我的第一位新型冠状病毒患者,是警车开道送来的。
那是1月24日,除夕。在隔离病区待命多时的我接到电话:一个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要转到我们病区来。

那时,我所在城市确诊的病人相对还比较少,我没有见过真的感染者。不禁想,病人会是什么状态?
放下电话,我叮嘱值班的护士做好准备,自己穿好防护服到防护楼的楼门口等待——
远处红蓝灯在路的尽头闪烁,我突然意识到,是警车开道。警车在距离防护楼门口10米远的时候停下了,后面的救护车继续朝前开,直到防护楼门口才停下。
救护车的门一打开,下来四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,他们在救护车门口一字排开,全部穿着防护服。大家都很沉默。
因为穿着防护服看不出谁是谁,也不认识谁是谁,我上前跟四个医护人员竖起大拇指,比了个“点赞”的手势。
我没有第一时间看到病人,脑子里不停地想,病人怎么样了?车上跟了四个人,会不会是抬着担架下来?
就在我好奇的时候,病人下了救护车——
自己走下来的。
我的第一感觉是,他不像个“病人”,他跟我这些年见到的病人完全不一样:因为戴着口罩看不清样子,我只能看到他口罩上方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,头顶有点秃。除了紧缩的眉头能让人感觉出他心事很重以外,看上去再普通不过。
他拿着一个背包自己走下车,像是回家路上突然被叫醒,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地方。
资料上写他姓万,比我大一点,我就喊他“老万”。
做完了交接,我对老万说:“您跟我走吧。”老万没说什么,只摆一摆手,算是跟我打了招呼。老万跟着我进了防护楼。
后来我才意识到,那是老万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最后一次看到外面的天空,吹到外面的风了。

我的“隔离”,比多数人要早。
1月15日,当大家还沉浸在采买年货、迎接新年的喜悦中,对“新型冠状病毒”这个名词并不了解的时候,我已经参与到了隔离病区的筹建当中。
从病区的划分到防护用品的储备,我在我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做着准备:接受培训,熟悉仪器操作......10天的时间,我和病区一起,一点点完成了“建设”。
因为要接诊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,我们清空了整栋楼作为“防护楼”,只留我们这一个病区,我们这一队人。
待命的时间里,整个病区空荡荡的,自己的脚步声在走廊里会发出巨大的回响,空旷、荒凉。整片病区像是和我一样,都在静静地等待。
我所在的医院是新型冠状病毒省级定点医院,整个隔离病区都是我的工位。从筹建那天起,我就一直在这片隔离病区里,见证着这里发生的一切。
直到1月24日,大年三十的上午,我和这片病区迎来了第一个确诊患者,老万。
隔离病区在2楼,电梯从1楼到2楼只要几秒,但我却觉得很慢。电梯里只有我和老万两个人,我们都没有说话。我特意去看老万的眼睛,但那双眼睛很空洞,里面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不知所措。
其实我想跟他说两句话,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他知道他被确诊了,我也知道,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,我也明白。
他没有看我,可能他对这几天围绕在自己身边这副装扮的人已经习惯了。他只是木讷地看着电梯上升的数字从1变到2。门开了,他在等我先出去。
进到隔离病房,关上安全门,我需要给老万做一些基础的检查。量体温的时候,护士有一些紧张,我说:“我来吧。”
我们用的是红外线感应的体温枪,但是戴着两层手套,手特别不灵活,我一不小心按错了按钮,体温枪关机又开机,我说实在不好意思,操作还不是特别熟练。一边测体温,一边趁机和老万说话,“你感觉怎么样?”
他抬起头,眼神明显错愕了一下,甚至有点惊慌,定定地看着我,开口说了第一句话,“你不怕我吗?”
我指了指防护服,说我穿着这些还怕你吗?“倒是你,你看我这样,不害怕吗?”
老万挂着口罩的耳朵动了动,也许是挤出了一个笑。“我很感谢您,被确诊以来,您是跟我说话离得最近的一个人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因为得病,老万没法跟别人接触,别人也不敢跟他接触,这是非常真实、无法逃避的“被隔离”,被关进笼子的感觉。
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疫情追踪的确诊病人,这个角色的转变来得太快了。

“确诊病人”入院隔离,和一般受了伤去医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
受伤了自己会疼,医院会有一套完整熟练的流程来处理,但从老万的感受来说,他现在只是有点发热,和普通感冒的症状几乎一样,却忽然被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,不能出去半步,谁都见不到。
没有缓冲,没有过渡,发现了就被控制了,心里其实很难一下接受。而被隔离的这些天里,可能也没有人进过老万的小屋子,跟他说说话。
想到这,我拍拍他的肩膀说:“老万,你不用担心,来到这里咱就是朋友了。”
我问老万,关于这个病你知道多少?
老万的表情很茫然,说他也不是很了解,只知道传染性特别强,跟当年的非典很像。
我说:“你说对了,是跟非典很像,但是当年我们面对SARS的时候,防护措施是12层口罩和传说中的‘板蓝根冲剂’,今天和当年可不一样了。”
其实说这话的时候,我也心虚。在这样一个大阵仗、大环境下,没有经验,没有措施,不知道怎么办,人不害怕是不可能的。
我唯一能参照的就是当年的SARS。那时我还在上高中,全国都在说“抗击非典,众志成城”,我没有概念。但现在,在新型冠状病毒战斗一线的人是我,我变成了抗击疫情的一份子。
回头想的时候才意识到,当年SARS时确诊了5千多人。就是说,在当时的防护条件下才感染了5千多人。其实SARS的传染性不强,是致病性强,当年那场战役的根源是防护不到位。随着病情的进展,慢慢提高了重视等级、防护等级,也才有了今天我身上的防护服。
当年抗击非典的人们和今天的我们一样,面对新型的疫情,每个人都是第一次。
“对于这个疾病,你比我了解得多,”我坦率地告诉老万,“你知道它有什么症状,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,你知道你的身体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。而我没有见过,更没有得过,你是我的‘第一例’。说实话,现在我没有什么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,请你理解,但是也请你相信我,我会和你一起面对它,好吗?”

我没法跟老万探讨具体的治疗方案,因为能给我们参考的数据太少了。1月24日,全国针对疫情的第一版试行方案还没有推出,根本没有所谓的“治疗方案”——我们没有药可用,也不知道什么管用。
我也知道,说出这句“我也不了解,我们一起面对”的话,其实很冒险,相当于在自己的病人面前袒露自己“不知道”。但从我接到老万的那一刻起,我就没有把他当成病人,而是想和他“做朋友”。这是我有意为之的。
病区筹建的时候,我曾站在隔离病房那扇窗户外面无数次设想过:如果我得了这个病,我是什么状态?我是什么心情?我需要什么?
一个可以说话的“朋友”,或许就是这样的时刻最能给我安慰的。
因为穿着防护服彼此都看不出样子,医护人员会在各自的防护服上做标记。
我在胸口左边写了自己的名字,又画上一颗红色的爱心,右边写了一句对老万说的话:别怕,我跟你在一起。

特殊时期,不光治疗手段需要“试”,连沟通方式,怎样面对确诊病人,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病人建立信任,都需要一点点摸索。
“现在全国对这个疾病都不是特别了解,我关注的可能是药物、治疗手段层面的东西,而你有切实体会,你把你的感受告诉我,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面对这个事,就没那么可怕了。”
当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,我并没有在老万的眼神中看到遗憾或是悲伤。老万反而打开了话匣子,慢慢开始说他是怎么确诊的,说他的感受,他的症状。
“老万,我没有把你当成一个‘病人’,你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?”
老万定定地看着我说:“我明白。”

我们请几个专家一起会诊了老万的病情,给他制定了适合的治疗方案。我密切关注着老万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和化验结果。除此之外,还每天固定两次,进病房和老万“话聊”。
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,谁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阶段或者是周期,但是病人的心理状态每分每秒都在变化,随着隔离时间的延长,一天一天,恐惧、焦虑都会加重。
治疗过程中,老万会不停地问——
“今天我的化验怎么样?”
“我肺的胸片拍得怎么样?”
或者“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?”
甚至“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你不敢在别人身上用的,可以给我试试!”
疫情防控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,就是像老万这样确诊患者的心理问题。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对家人的愧疚,一人确诊,全家都要被隔离。这个过程中他们见不到家人,我们就是他们每天能够见到的唯一对象。
老万的隔离房间原本是一个6人间,但是现在只有他一张床。房间特别大,大到有点空旷。有阳台,有卫生间,阳台外面就能看到一个小公园。遗憾的是老万只能在房间内活动,不能走出房间。
每次跟老万聊天,我都会格外留意老万的反应,从他的反应里判断他的状态。
我需要的并不是他听我的,或是信我的,我需要他参与进来——我教老万看他的化验结果,给他讲解CT怎样看,“你看你原有的病灶现在都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了,这说明,我们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!”
CT的前后对比,一点点细微的变化,我都指给他看。只有他动起来了,他的精力在我说的话上,才不那么容易胡思乱想,心理压力也会小。

其实,感染性疾病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,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,并不能杀灭。所以说人很重要,自己很重要。
而对于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,最重要的莫过于“希望”。

有天,我发现老万特别烦躁,一见到我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,着急地说:“您能帮我个忙吗?”
我赶紧问怎么了,他说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去见过父亲,“现在我被确诊了,我父亲也被强制隔离了,我父亲80多岁的人了,生活不能自理,脾气又倔,我这实在是没办法了......”
老万听说父亲一直抗拒隔离,特别不配合,非常担心。“您能帮我协调一下,让我老婆跟我父亲在一块隔离,能照应一下,或者在家隔离吗?”
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因为牵涉到两个医院,我没有权利去干涉隔离政策,但是作为老万的朋友,我知道这个电话对他来说有多重要。
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疾控中心,说明了情况。疾控中心很重视老万的情况,答应尽量协调。
第二天老万的家人就过去照顾老万父亲了,当天下午,老万父亲的咽拭子核酸监测显示阴性,被获准居家隔离。
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万。老万的脸被口罩遮盖,但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热切地看着我,眼圈渐渐红了。老万没说话,却主动握了握我的手。
我正在用我的方式支撑老万参与到自己身体的这场“保卫战”中。

当天晚上,同事们都去清洁区吃饭了,病区里的病人们都睡觉了,我一个人在隔离病区值班,只是值班而已,却几乎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小时。
那一小时里,我接触不到任何人,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艰难的呼吸声,能看到的只有护目镜前面这一点点视野。
我忽然想打电话,打给谁都行,我想跟人说话,我想周围有个人,我不想独自承受这一刻的孤独。

白天,我在病人、同事面前是“小太阳”,是带来希望和光亮的人。但夜晚,在隔离病区的走廊里,待眼前的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,我终于能面对我自己,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撑不住的时候。
我在隔离病区里进进出出这么久,但一想到那晚近乎静止的一小时,就感到绝望。
那一刻,我觉得自己更懂老万的心情了。
老万是家里的老三,他自己在,另外两个哥哥都在我们这个城市。
大年初一,老万的哥哥来给老万送饺子了。
哥哥一见我面就拉住我,说带了两份饺子来,一份给老万,一份给我。“您不用担心,这个肯定是干净的。”
但是我确实不能吃老万的饺子,因为我们的病区里,所有物品都是单向流动,病人的物品是从病源通道进来的,一旦进来只能刹住,不能再往里走。
哥哥转而给我拜年,“您辛苦了。我弟打电话都说了,我知道您很勇敢,但是您要保护好自己。今天大年初一,我给您拜个年吧。”
说完给我深深鞠了一躬。
那一刻我真的差点绷不住。我突然意识到,我们和病人之间其实是互相支撑的。
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是战士,在战场上坚决不能退缩,不能有任何思想波动。但其实我也清楚,自己就是个穿着白大褂的普通人。
从1月15日开始一直到现在,没有昼夜、不知阴晴、连续不断地工作,听见老万哥哥那句话的时候,我特别想家,想往家打个电话。
我想告诉老万,也告诉那一晚的自己:别怕,有很多人跟我们在一起。

故事发出前,魏医生告诉我,老万已经治愈出院,给他留了一封信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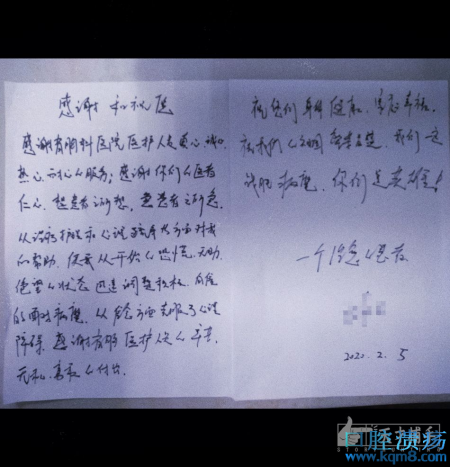
这封信,老万不只是写给主治医生的,更是写给“朋友”的。 老万住院期间,新型肺炎的治愈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,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,并不能杀灭。所以说人很重要,自己很重要。 那个可以说话的朋友,大概才是老万在特殊时期得到“最好的药”。 对于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,最重要的莫过于“希望”。 魏医生记录下老万的故事,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药。 这是《瘟疫瘟疫你快走》第五篇,一个关于“治愈”的故事。 明晚22:04,我换个方式,继续陪着你。